还吾庄子 沈善增 扫描版
文章类别:
- 21 11 月, 2022
- 0 条评论

 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
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你必须注册后才能投票!
快捷索引
/thumb.jpg)
概述:
《还吾庄子》以现代人的观点全面阐述了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,全书知识丰富,解说详尽,通俗易懂,不失为一本让人觉得不得不看之书。读中国书不能不读《庄子》,不能不读《逐吾庄子》。以前读一些讲解佛经的著述,开篇都是从解题着手,而且,从总到分,洋洋洒洒要讲一大篇。一个词一个词地落实、引申,一个经题可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,觉得这样非常烦琐。因此,我第一稿注《逍遥游》时,是没有题解的。但实际注下来,发现直接切入正文,效果也未必佳。古人解经从题目着手,自有他的道理。尤其是我这次移宫换羽,改走一本正经以庄注庄的路子,考虑再三,还是走这条老路,才是终南捷径。因为从解题进入,至少有三条好处。
首先,可以看到,《庄子》一书,是作者精心写成,而非由后学辑录而成。
《庄子》,据(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共有五十二篇。到晋代的司马彪注本,计有内篇七,外篇二十八,杂篇十四,解说三,合五十二篇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注本——郭象注本,只剩下内篇七,外篇十五,杂篇十一,合三十三篇。少掉的十九篇,不是郭象没看到,而是被他认定不是出自庄子之手,有损庄子大家形象而删去的。在两晋时代,对五十二篇中哪些是庄子写的,哪些是后人辑录的,哪些是不肖之徒假借庄子名义伪托窜入的,各家意见很不一致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,就是内篇七篇一定出自庄子本人之手,是他老人家一字一句抠出来的,而不是别人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的。形成这条共识的一条充足的理由,就是七篇的题目。七个题目统一都是三个字,而且这三个字明显是根据整篇的中心思想概括拟就的;不像外篇与杂篇,随取篇首的二或三字为题。外篇与杂篇的取题法,完全因袭《论语》的作派。《论语》是后人辑录的,所以各家据之怀疑外篇与杂篇中也有部分甚或全部是后人辑录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反过来可以证明内篇是庄子亲自动手写的。
然而这点共识,到近代还是有人提出质疑。齐思和在《庄子引得)的“序’中说:“至于内七篇,则从来学者,皆以为庄周所自撰,疑之者尚鲜。成玄英疏序云:‘内篇理深,故于篇外,别立篇名。外篇以去,即取篇首二字为题。故陈景元曰:“内七篇目,漆园所命也。”’今按,内七篇目是否为庄子所自定,固难质言,而其著述体例,与外篇杂篇,截然有别,则极明显。以梁任公之好辨古书,亦谓:‘内篇为庄子自作,无问题。’然余观《齐物论》篇称:‘昭文之鼓琴也,。师旷之枝策也,惠施之据梧也,三子之知几乎!皆其盛者也。故载之末年。’庄周乃惠施之友,若是篇果庄所自为,安得列惠施于古贤之林耶?又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德充符》等篇,皆于篇末附记庄周轶事,亦不似庄周所自为者。再以著述之体裁观之。战国以前,无私人著述之事,章学诚已言之矣。最早之私人著述,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,皆用问答之体。殆出于门人后学所记。后儒往往分为篇章,以便诵习,即以篇首二字名其篇。若夫先立一题,然后执笔著论,如《荀子)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等书,则战国末年之事。是则内七篇,殆亦后学所述,未必即出于庄周之手欤?”
之所以把齐思和先生这段话引在这里,是因为我觉得此中很典型地透露出一种习气,以疑古为能事。这种动辄把不合己意的篇章语句指为后人伪托窜入,乃至抓住几条就把整本书定为伪书,我在读注庄各家乃至先秦诸子的注本时,经常碰到。开始对这样做学问的先生很有些敬畏感,因为他们说起话来指手划脚的腔调,实在是权威得很,你不服还真不行。像齐思和先生
这么质疑,是算谦虚得不得了的。读他们这些论断,常感到非常庆幸,没有他们火眼金睛指出来,自己被伪“庄子”骗了卖了还不知道,多么危险啊!等到后来我按照他们的指点,感到庄子的话怎么越读越糊涂,才发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头。我好不容易决定不理这些权威人士,从另外的途径去解《庄子》。待我总算从他们布下的八卦阵中走出来,接近了本来的庄子,我才明白那些权威意见除了别有用心的篡改外,大多是由他们的一孔之见发出的自说自话。
就以齐先生质疑内篇非庄子自作的三条理由来说,都是站不大住脚的。
其一、庄子与惠施是朋友,他怎么会把惠施列到“古贤”中去?
从《庄子》中看,两人确实是朋友,但《徐无鬼》篇中有庄子过惠子之墓,发出伤心感慨的片段。所以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把惠施与昭文、师旷并称为“皆其盛者也,故载之末年”,完全有这可能,庄周为什么不可以在惠施死后才开始著书立说呢?而且,惠施死了,庄子失去了探讨辩论的对手,才把求道热忱化作笔底波澜,也是顺理成章的。至于说庄子这段话是“列惠施于古贤之林’,那是齐先生的误解所致。以我看到的注庄各家,没有一个弄明白庄子为什么在这段话里要把昭文、师旷与惠施并举。齐先生就想当然地把三者的共同点理解为“贤”了,其实与“贤”是不搭界的。到底共同点是什么,以后注到时再详说,这里卖个关子。此外只需说明,“贤”乃妄测,遑论“古贤”,齐先生的质问落了个空。
在庄子时代,阴阳五行学说才初露端倪,还没有发展为繁复的系统理论,所以,后面的六种意见,因其太系统、太全息、太数理化,显见不会是庄子所言之“六气”。从庄子说“六气”不加任何解说来看,这“六气”应该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概念。考察一下,只有司马彪的说法可能性最大。此说又有《左传·昭元年》所载医和之言可作佐证。《庄子》中还有一处提到“六气”,见于《在宥》篇:“云将曰:‘天气不和,地气郁结,六气不调,四时不节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,以育群生,为之奈何?”从这段话中看,“六气”不是“天气”与“地气”,故而李颐、王逸把“天玄”、“地黄”列入“六气”之中是不对的;但是,前有“天气”、“地气”,后有“四时”,可见“六气”又与气候有关,所以,“阴,阳,风,雨,晦,明”等可见的天象气候变化为“六气’的内容,也是很妥贴的。从这段话可见,古人对天象气候,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法。“天气”、“地气”是一种分法,重在空间的广大、对万物的涵养。“四时”是一种分法,重在周期性的变化。“六气”又是一种分类法,重在现象的区别。“天地”强调根本性,“四时”强调周期性,“六气”强调现象特性。“天地”为体,“四时”为常(也即体的必然表现),“六气”为用(体的偶然表现,尽管在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,偶然性受到必然性的制约,但表现出来,不易看见规律性,像是一种意志行为)。故而,“乘天地之正”后面,不能说“御四时之辩”,而只能说“御六气之辩’。这两个分句,照佛家之言来说,“乘天地之正”就是证体,就是禅宗所说“明心见性”,密宗所说“胎藏部”、“莲花藏”;“御六气之辩”就是致用,就是显教而说“普度众生”,密宗所说“金刚部”、“金刚地’。如果要加个“四时”进去,只能是“通四时之变”。“六气’中“阴阳”、“晦明’可以互变,“风雨”是相成而不一定能互变,“阴阳”、“风雨’、“晦明”之间则没有什么必然联系,因此,这个“辩”,只能训为“别”,释为“变”是不确切的。
只有“乘天地之正”,才能“御六气之辩”,前者是必要条件,后者是可能结果。而这两者,又构成“游天穷”的必要条件。“游无穷”才是庄子追求的目标,才是得道的理想境界。这才是“逍遥”。达到“逍遥’的才可称为“至人”。至人已证大道,已起大用,已得大自在,像这样的人,他还会受到什么条件的限制呢?“彼且恶乎待哉?”
“待”也是庄子的语汇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。《说文》:“待,埃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今人易其语日:‘等’。”从“等待”这原初义,引申出“依靠,仗恃”之义。因为”等待”必须站在一个地方守候着,这个立足点,也就是立场,由立场引出了凭恃。《商君书·农战》:“国待农战而安,主待农战而尊。”又由“依仗”之义,引申出“需要、必须”之义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:“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。”庄子就是在“依仗”与“必须”之义上使用“待”的,可意译为“立场”与“条件”。在译为“条件”时,应考虑到其中蕴有“立场”的意思,这“条件”是指有关“立场”、“依据”的重大条件。“彼且恶乎待哉?”以佛家用语说,就是:“那人还有什么相可执著呢?”
为什么说能“乘天地之正,御六气之辩”,即可“无待”呢?因为达到这一境界,个体就与本体(道)完全同一了,他的自由度等同于道,是无穷大的。无穷大的个体,也就等于个体的消亡,因此,才可以说是“无我”。而这个“无我(小我)”的”我”,才是真正的“我”。因为“我”的本义是“主宰”,也就是自由意志。只有具有无穷大的自由意志,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,这样的自由意志,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由之处。
需要指出的是,东方哲学,佛家与道家,从一上来就明确这自由意志不是西方神学所谓的“全知全能”,为所欲为。在《序》中我已引过元圭禅师的“佛有三能三不能”之说。这里,庄子也确立了“游无穷”的逻辑关系,以“乘天地之正”为前提。因此,如果一定要用“唯物’与“唯心”的二元对立来套,那么,佛家与道家都可以统战进来壮大“唯物主义”的阵营。因为他们都认为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规律存在,都认为觉悟者就是完全能穷尽、顺应、掌握这些规律的人。当然,用“唯物”、“唯心”这样的理论框架来套佛家与道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,因为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,简单类比,无助于
弄清其本来面目,只有越抹越糊涂。我们还是以了解庄子的原意为目的。
以上说了我对庄子这几句话的注解,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郭象是怎么注的。
“天地者,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,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自然者,不为而自然者也。故大鹏之能高,斥鴳之能下;椿木之能长,朝菌之能短;凡此皆自然之所能,非为之所能也。不为而自能,所以为正也。故乘天地之正者,即是顺万物之性也;御六气之辩者,即是游变化之涂也。如斯以往,则何往而有穷哉?所遇斯乘,又将恶乎待哉?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。苟有待焉,则虽列子之轻妙,犹不能以无风而行,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,而况大鹏乎?夫唯与物冥,而循大变者,为能无待而常通,岂自通而已哉?又,顺有待者不失其所待,所待不失,则同于大通矣。故有待、无待,吾所不能齐也;至于各安其性,天机自张,受而不知,则吾所不能殊也。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,况有待者之巨细乎?”
郭象这段注特别长,可能是所有郭注中最长的一段。郭注很少这样长篇大论,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故千百年来,不管人们怎么质疑,郭象总是注庄的第一权威人士。
内容截图:
/thumb.jpg)
会员福利
同类文章
文章类别:
本文链接: https://www.books51.com/264447.html
【点击下方链接,复制 & 分享文章网址】
还吾庄子 沈善增 扫描版 → https://www.books51.com/264447.html |
上一篇: 还吾老子 沈善增 文字版
下一篇: 练打暗器秘诀 金倜生 扫描版

 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
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你必须注册后才能投票!

/thumb.jpg)
/thumb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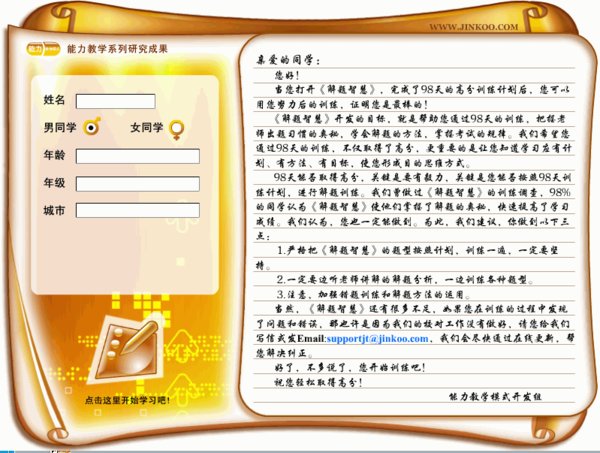

最新评论